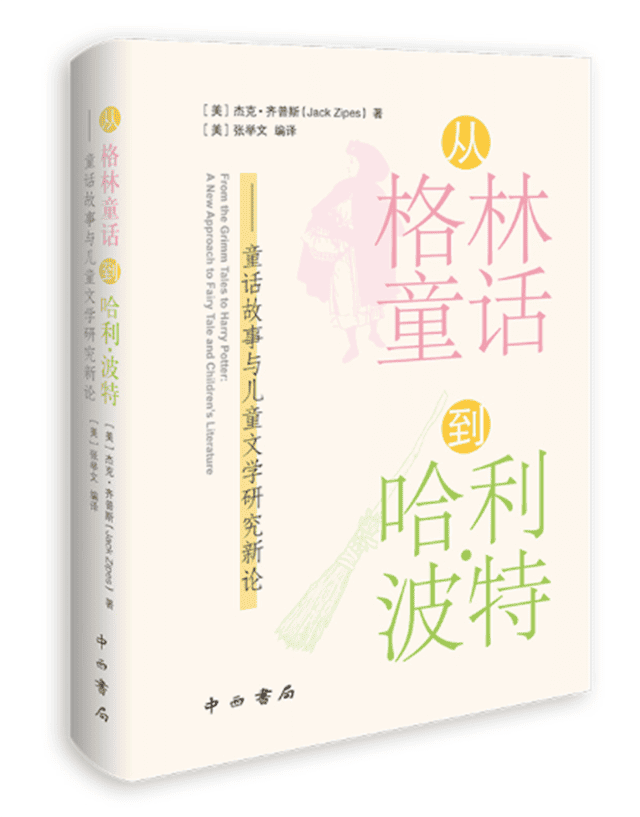
作者: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
译者:蒋海军、蒋连琼
【延续自《老鼠、仙女、巫师和食人魔的激进道德观:认真对待儿童文学》(一)】
这显然是为什么“哈利•.波特”书籍在美国和英国社会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像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弗兰西斯卡• 莉亚•布洛克(Francesca Lia Block)、唐娜•乔•纳波利(Donna Jo Napoli)和威廉•史代格(William Steig)等给孩子写书的奇幻文学作家最近都享有如此大的知名度。它们都与巫师、仙女、老鼠和食人魔打交道,就像许多其他当代作家和插画家一样。这份名单是无法终结的,因此,我想缩小我的注意力,比较和对比其中的一些作者,用来传递其激进道德信息的叙事技巧。我之所以要把重点放在童话和奇幻文学的激进道德上,是因为它是理解所有故事的本质的关键。正如杰出 的心理学家杰罗姆 • 布鲁纳 (Jerome Bruner) 在他的著作《有意义的行为》(Acts of Meaning)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伯克( B u r k e )的意义上讲,戏剧主义侧重于从具有道值后果的规范中衍生出来的衍生物,其与合法性、道德承诺 、价值观相关。因此,故事必然与道德价值、适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的不确定性有关。麻烦这个概念的前提是,行动应该适当地适应目标,场景和乐器相适,等等。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指出的,故事是在合法性范围内进行的探索。他们表现得‘栩栩如生’,如果不加以调整,就会有道德说明的麻烦。如果像后现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失衡现象隐约存在,那是因为叙述者试图颠覆传统的叙事方式,从而使故事具有道德立场。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采取一种道德立场,即使这是一种违背道德立场的道德立场。”
我的目的是质疑像“哈利•波特”这样的作品的社会和道德价值,提出对年轻读者来说童话和幻想写作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并介绍一些作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尽管并非没有错误,但却比“哈利•波特”和常见的一些文学作品更需要年轻读者的关注。我这样做是作为一个毫不隐晦的成年评论家,认为儿童文学应该受到我们为那些给成年人写作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所设定的同样高的美学和道德标准(的评判)。与此同时,我对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故事的评论,是对更激进的变革的呼吁,并与我们在过去的4个世纪中所见证的在所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发生的激进变革相衬。文化生产领域的发明需要作家和艺术家的回应,因为新科技改变了我们传达各种故事的方式,并形成了文化产业有效性的基础。当然,如果没有开放讨论当代社会有害趋势的可能替代方案,就很容易谴责文化产业的同质化故事和文化以及道德妥协。凭借新技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伊丽扎•德雷桑(Eliza Dresang)在她的著作《激进的变化:数字时代的青年书籍》(Radical Change: Book for Youth in a Digital Age)中评论道:
传统的青年文学既是线性的(即逐步阅读,“单向”进展),也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内容显然与之前的内容有关)。但数字时代的书籍是以不同的方式设计的。数字时代的孩子能够从文本片段中获取“位和字节”的信息,这些片段不一定是从头到尾或从左到右排列成直线。这是非线性文本。它也可能是连续性的。有时年轻读者必须寻找自己的路径,建立自己的顺序。读者必须用自己的眼睛“指向并点击”以找到所需内容。这种二维数字现象在本书中被称为手持式超文本。超文本是指将文本分支并允许读者选择的文本,它通常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但在这本书中,它被用来描述手持设备中类似超文本的体验。
德雷桑特别热衷于互联网和大众媒体的技术进步,因为它们允许年轻人进行更多的活动和思想交流,并允许对儿童文学进行追本溯源的试验。作家和艺术家通过使用新格式的图形来回应新技术和需求,通过文字和图片创造新层次的协同作用,在非线性和非连续性的文本组织中提供多层意义,通过具有多视角的作品为读者或观众提供更多交互式可能性以及处理那些有开放结局的以前被禁止的情节中的主题、人物和场景。
德雷桑认为,年轻人没有必要通过直接上网来接触数字世界的热门话题,因为它们充斥于每日新闻和电视及在操场和商场的谈话中。一些成年人所采取的立场(即在这本书中所采取的)是,与其限制接触,不如向年轻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能,使他们能认识和处理威胁到他们和其他人应该得到的尊重的局势。孩子们总是阅读为成年人写的书,即使面向他们的文学作品已经得到发展。如果孩子每天都接触成人世界,为什么还要有单独的青少年文学?因为儿童确实能够从符合他们的兴趣和生活背景的文学中受益。他们所不能从中受益的,是那些假定他们不能处理复杂的事情的“通俗”文学。
在某种程度上,德雷桑对她所称的数字世界有点不加批判,因为通过互联网和新技术,并不是好像就一切都已经变得开放和可访问了。许多评论家质疑世界的“全球化”,并指出美国统治的文化是正是通过德雷桑认为的开放话语的互联网发生的。比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
新媒体被广泛赞美的“互动性”,显而易见是夸大其词;人们更应该谈论的是“互动的单向媒介”。与学术界相比,新的全球精英往往倾向于相信,互联网和网络并不适合所有人,也不太可能被普遍使用。甚至那些获得访问权限的人也只可在供应商设定的框架内做出选择,供应商请他们“花费时间和金钱在他们提供的众多套餐之间进行选择”。至于其他,留在卫星网络或有线电视的部分并没有像屏幕两侧之间的对称部分那么多,并且只是纯粹和不加思考地观看。他们看的是什么?他们只看少数受关注的名人。
因此,媒体的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积极变化。此外,德雷桑没有充分研究儿童由于长期接触“声音字节”和“碎片图像”所引起的注意力不足和注意力分散的问题。这些不是激进问题,而是非常流行和常见的问题。长期接触闪烁的图像、文字、声音和多维文本会如何影响认知过程?有身体和神经方面的影响吗?年轻人是否以激进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便他们能够紧跟潮流,成为更激进的消费者?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很明显,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故事中发展叙事策略和进行艺术创作,都会采取道德立场,不管其结局是开放式的还是封闭式。实际上,在书籍制作、设计以及屏幕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是否都是积极的,仍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德雷桑关于数字时代儿童书籍变化的论点很重要,因为她强调需要尊重和给年轻人一些挑战,同时为他们提供联系,使他们能够认识到是什么导致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识别导致这些问题的“邪恶”,并且认识到导致这些问题的“邪恶”大部分来自成人行为。
谈到邪恶,现在是时候转向一些主要为年轻人创作的传统、激进的童话故事和奇幻作品的例子,并评估他们如何描绘邪恶和将其融入作品的背景。由于我已经在我的书《魔杖与魔石》中花大篇幅写了关于“哈利•波特”小说的传统性,我想总结一下我对罗琳作品的评论,然后讨论普尔曼、布洛克、纳波利和史代格的更多创新试验,并评估他们独特的幻想试验及其道德寓意的激进本质。
毫无疑问,“哈利•波特”系列书籍写得非常巧妙,为年轻读者提供了一种希望和赋权感,但它们也是非常传统的、可预测的、在意识形态上保守的,并且在恢复男性霸权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现在,我知道通过发表这样看似严厉的声明,在政治上,我可能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我不是在谴责书籍,也不想让它们受到审查或禁止。让我重申一下,乍一看,这些小说似乎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息:一个天才小孤儿,被一个名叫伏地魔的邪恶角色所追捕,设法战胜了他的敌人,并在克服逆境的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非凡的想象力。这是所有4部“哈利•波特”小说中充满希望的故事情节,但不幸的是,这是每一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其中哈利和所有人物基本保持相同,并在小说后重复小说中的相同动作和姿势:哈利,一个灰姑娘般的男孩,在一个庸俗的人家收到弗农•德思礼、佩妮•德思礼以及他们的流氓儿子达德利的虐待;哈利得救了,因为他必须在秋天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哈利在魁地奇球赛中表现出他是多么优秀的运动员,在学校表现出色,并且避免了伏地魔的爪子;哈利回到家中时是一个英雄,但不会得到他应得的认可。这一情节类似于最小的儿子或裁缝的传统童话故事,他们出发到世界各地去创造自己的印记,征服巨人、龙或恶棍,甚至作为君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已经听过或读过这类故事数百甚至数千次,除非有创新的变化,否则它仍然是男性力量的胜利。就“哈利•波特”的书籍而言,虽然有一个名叫赫敏的聪明女孩,但这部小说的大多数行为和关注都涉及男孩和男人使用和滥用魔杖和扫帚。小说的背景是一所精英魔法学校,在学校本身的运动场庆祝比赛,主要人物被他们的权力追求所困扰。小说中的邪恶与嗜血的伏地魔联系在一起,后者杀死了哈利的父母,并试图通过完全控制宇宙来统治世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种对邪恶的描绘相当简单。邪恶是伟大的压迫者、缠绕者、欺凌者、虐待狂,无法控制的黑暗力量,邪恶甚至可能潜伏在哈利身上。最后,罗琳似乎在说哈利必须通过他的经验来学习以抵制自己的邪恶,并用他的魔杖来造福所有人。但什么是好的?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勤奋用功的童子军吗?
“哈利•波特”小说的黑白道德没有任何问题,只是说,当世界被描绘成如此传统的黑白时总会出现问题。当邪恶力量从未在某种背景下被设定并且仍然完全神秘时,也会出现问题。并不是说邪恶是可以被真正知道的,但是在可预测的续发事件和传统的方式中有一些错误,在这种传统的方式中,哈利被描绘为被选中的一个对抗黑暗势力的人。在描绘哈利的过程中,与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或洛奇(Rocky)略微不同,后者尽管是弱者,但他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正是哈利,作为一个永远无法被打败的明星,破坏了这个故事的道德信息。由于邪恶是无定形的,哈利从不知道他在打什么,在小说中,唯一变得重要的是哈利赢得并征服了未知的变形攻击者。认知过程通过在每部小说结尾处解开谜团完成,这是一个错误的过程,因为哈利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邪恶。罗琳似乎在提议,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我们内外的邪恶,我们必须通过正义的行为来证明我们是善的。这让人联想到加尔文主义者的信条。很容易让人想到这可能是对的,即拥有魔力的人可以决定道德标准。事实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们控制文化产业的人可以决定品味和道德。哈利似乎是大众媒体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的反对者,但他所有的训练都是在魔法领域,我们从鲍姆(Baum)的《绿野仙踪》中了解到这一点,巫师可能是终极骗子。哈利是否会长大成为骗子是值得怀疑的,但在前4部小说中,他显示出被自己的艺术和魔力消耗的明显迹象。我们留下了自我吸收和自我消费,可能为某种自我实现铺平道路。然而,罗琳似乎在推崇名人崇拜,难道没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吗?难道不是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平庸之恶”所造成的严重问题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如果他们想要理解今天的邪恶,那么名人、惯例和平庸之间不是有联系的吗?这些都是罗琳小说中不受欢迎的问题,邪恶和邪恶的社会本质仍然超出了哈利和当下罗琳小说的读者的视野。
菲利普•普尔曼在他的一系列非凡的奇幻小说中的邪恶观念比罗琳在她的“波特”系列中所展现的更加复杂,对读者来说更具挑战性。他不断建立联系,使读者能够理解阻碍他们发展的准确的力量,并混淆他们对现实世界中矛盾的看法。在他的“激进”三部曲中,他的黑质三部曲,包括《黄金罗盘》(1995)、《魔法神刀》(1997)和《琥珀望远镜》(2000),有来自死亡世界的战争、谋杀、沉闷的场景,有我们在小说中遇到的虐待狂和残酷的行为以及虚伪的恶魔。但是这些作品并没有使读者感到沮丧,相反,是令人振奋和明晰的,并揭示了是什么构成了邪恶,且反思了其他的生活方式。有多视角,随时间变化和非连续的故事情节需要,读者全神贯注地集中注意力。总体而言,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充满了乌托邦的精神:普尔曼阐明了两个12岁的孩子,即莱拉和威尔,如何勇敢地与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中的野蛮环境作斗争。黑暗暴露了它的本质,即邪恶力量为神权服务,扭曲了它的崇拜者的灵魂和思想。这种表现良好的邪恶反映了黑暗如何威胁着我们自己的世界,以及我们如何用谎言和欺骗蒙蔽儿童。普尔曼坦率地批评有组织的宗教和政府机构,它们促进了强权政治并形成了当代世界邪恶的本质。像弥尔顿的《失乐园》一样,普尔曼的寓言在社会政治上的姿态是明确的。不同之处在于普尔曼比弥尔顿更乐观,他的三部曲可以被称为“复乐园”。
(待续)
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2022)。《从格林童话到哈利•波特:童话故事与儿童文学研究新论》。上海:中西书局,304-331页。